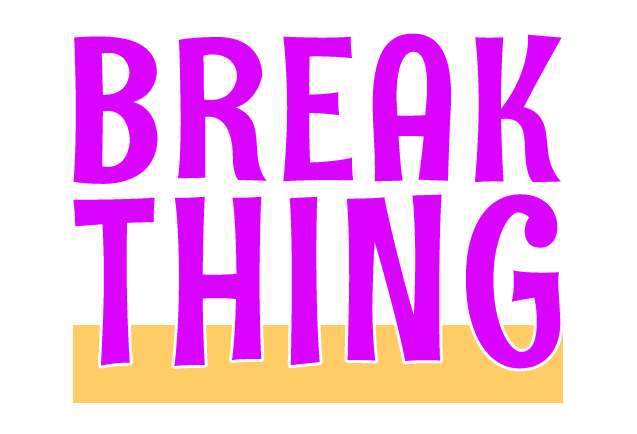7月18日,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开全會,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經投票再次當選歐盟委員會主席。新華社記者 趙丁喆攝

7月4日,英國議會下院選舉投票开始。圖爲一名男子在一處投票站投票後離开。新華社記者 李穎攝
7月16日,梅措拉再次當選歐洲議會議長;7月18日,婭埃爾·布朗-皮韋連任法國國民議會議長;同是18日,馮德萊恩再次當選歐盟委員會主席。
三位女性領導人的連任,讓歐洲政治看似“風平浪靜”。實際上,大風早已“侵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豈能輕易地止於草莽之間。
6月以來,歐洲議會選舉、英國大選和法國議會選舉三場重要選舉,已讓歐洲社會分化以及政治上的碎片化、極端化趨勢暴露無遺。執政者普遍遭遇挫折,民衆對傳統政治人物和政黨無感、無奈,“疑歐”政治力量影響急升,歐洲未來不確定性前所未有。
“幻滅後的反叛”
三場選舉各不相同,結果迥異,比如英國大選產生了一個穩定多數政府,而法國則產生所謂的懸浮議會,即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獲得絕對多數。但共性也非常突出,那就是執政者遭到選民的反叛,歐洲社會的不滿甚至憤怒情緒彌漫。
其一,歐洲政治碎片化的發展趨勢加快加強。過去20余年來,歐洲政治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碎片化。大黨不大,小黨不小,更多的政黨進入議會,三黨、四黨甚至五黨、六黨才能組成執政聯盟。
在歐洲議會選舉中,以往僅憑中右翼的人民黨及中左翼的社會黨兩大黨團就能獲得穩定過半的多數議席,但此次人民黨團、社會黨團加上復興歐洲黨團才取得勉強過半席位。
在法國議會選舉中,議席的分散程度比2022年更嚴重。在英國議會選舉中,工黨在議會下院650個席位中獲得412席,看似一面倒,但實際上得益於所謂贏者通喫的選舉制度。工黨的得票率只有34%,也就是說,英國社會也非常分化、政治高度碎片化。
其二,歐洲政治極端化的發展趨勢加快加強。觀察過去幾十年來的歐洲議會選舉,盡管時有起伏,但受到主流政治排斥的所謂極端政黨,特別是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得票率一直在穩步快速增長。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共獲得約五分之一的議席,而此次已獲四分之一的席位。
在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盡管面臨幾乎所有其他黨派的擠壓,但是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一舉成爲法國第一大政黨,在國民議會所獲議席從2012年只有2席,到2022年獲得89席,再到此次選舉獲得143席。
在德國,2013年才成立的極右翼德國選擇黨很快便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此次所獲歐洲議會席位也超過執政三黨,成爲僅次於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全德第二大黨。
在意大利,執政的極右翼政黨意大利兄弟黨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再次獲勝。
其三,歐洲政治“遊戲化”的發展趨勢加快加強。歐洲政治運作失靈,不是一個新現象。過去幾十年來,不論是換黨還是換人,都解決不了歐洲民衆關心的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民衆對政治、選舉的無奈感和幻滅感,對傳統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都在增強。
歐洲國家自己也認爲,歐洲議會選舉就是“抗議投票”,也就是說,民衆借5年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發泄對本國執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不滿。但這樣產生的歐洲議會,其民意的代表性和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只會更加凸顯。
法國第五共和的初衷就是確保產生一個強有力的總統和政府,但2022年就沒能產生一個多數政府。此次國民議會選舉更是加劇了政府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好似正在回歸第四共和時的混亂狀態。英國工黨僅憑34%的得票率就能獲多數席位,根本體現不了多數民意,只會進一步增強民衆對政治的厭惡和幻滅感。
長期難解的困局
民心思變的背後,是歐洲長期難解的一系列問題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是經濟低迷。21世紀以來的20年可謂是歐洲失去的20年,歐洲經濟持續遭受多重危機衝擊,平均增長率不到美國的一半,希臘、意大利等部分國家經濟總量至今仍未能恢復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
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更是對歐洲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包括通貨膨脹、生活成本危機等。2023年,作爲歐洲經濟核心的歐元區僅增長0.5%,歐盟11個成員國陷入負增長,最大經濟體德國衰退0.3%;2024年,歐元區預計僅將微弱增長0.8%,且這可能還是相對樂觀的估計。
英國自脫歐後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2023年陷入衰退,2024年僅將微弱增長0.7%,71%的民衆認爲脫歐後經濟形勢惡化。此外,英法等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都在快速增長,未來經濟發展難以樂觀。
二是社會分化。總體看,歐洲的社會分化仍在持續發展,特別是精英階層與普通民衆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大。
歐洲所謂的精英階層,無論左右,在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等地緣政治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價值觀等問題上看法大體一致,遵守政治正確,趨同性明顯,壓制不同意見,動輒扣帽子,主導着歐洲內外敘事和話語權。
而普通民衆的正當訴求和不同意見,輕則被忽視,重則遭壓制。比如,俄烏衝突帶來的生活成本危機、難民問題、能源問題以及烏克蘭農產品問題等,嚴重衝擊歐洲中產及底層民衆生活,但這被精英階層視爲理所當然,是必須付出的代價。2024年以來全歐範圍內的農民抗議示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不只是農業,其他行業的抗議示威也此起彼伏。
越來越多的歐洲民衆不滿本國政治體系和政治人物,比如相當多的法國人認爲總統馬克龍是“富人總統”。部分民衆將難民及非法移民的增加歸咎於歐盟,因此,主張採取強硬政策、收回國家主權的極右翼政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由於無法有效回應民衆關切,歐盟越來越被認爲是一個高高在上、脫離民衆的官僚機構;而與此同時,成員國又因將一部分權力上交歐盟而行動受限,無法及時有效回應民衆關切。
歐洲一體化的實質是逐步減少國家主權,同時逐步構建歐洲主權。在這一過程中,歐洲主權與國家主權的矛盾也持續累積。這是一個有歐洲特色的結構性問題,越來越尖銳,而且進退兩難。
深愁中的迷思
战後幾十年來,歐盟和歐洲一體化多次遭遇危機,但最終都能克難前行,這就是所謂的“危機驅動論”。但與過去不同,當下歐洲面臨的問題和危機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全面的,經濟、社會、地緣政治與安全問題交織,更加復雜難解。而且,當前歐洲在全球處於一個更爲不利的地位,應對和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下降。
歐洲更加難以推進战略自主。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洲形成了對美國經濟、金融、能源以及安全等領域的全方位依賴,遠超以往的冷战時期。與之相應,歐洲出現了馬克龍所擔心的“附庸化”趨勢,即作爲美國的依附者,即使很多情況下有損自身利益,也不得不更多服務於美國利益。歐洲的安全、能源、經濟、金融政策全面受制於美國,難以獨立發展,社會更加分化,外部環境也更加嚴峻。
歐洲更加難以推動一體化和結構性改革。一體化是歐洲力量的最重要來源,但一體化就像騎自行車一樣,不往前走就會出問題。自2009年《裏斯本條約》生效以來,歐盟多年來只是修修補補,再未能修改條約,解決一體化中的系列結構性問題。相反,南北矛盾、東西矛盾、德法分歧等問題持續累積。隨着政治碎片化、極端化的持續發展,法、德政府均更爲弱勢,未來一體化前景暗淡。
歐洲更加難以推行理性務實的內外政策。當下的歐洲,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持續發酵,大大壓縮理性思考和務實政策空間,政治正確越來越成爲難以碰觸的禁忌,保守、內傾、排外正成爲潮流,堡壘化趨勢愈益明顯,而歐盟過去的繁榮和影響力正是來源於开放發展和包容性發展。
可以說,當下歐盟的經濟困境,很大程度上與歐盟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思維有關。理性、務實和包容的缺乏只會進一步加大歐洲經濟困境,並導致更多的社會、政治問題,從而讓歐洲更不安全,形成惡性循環。
“疑歐”圍城之際,花自飄零水自流?
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歐洲如何選擇,對自身乃至世界來說都關系重大。毫無疑問的是,自主自立、开放包容、理性務實的發展之路會讓歐洲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有利於歐洲,也有利於世界。
(作者:張 健,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標題:歐洲苦“選”:一種迷思,兩處深愁
地址:https://www.breakthing.com/post/135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