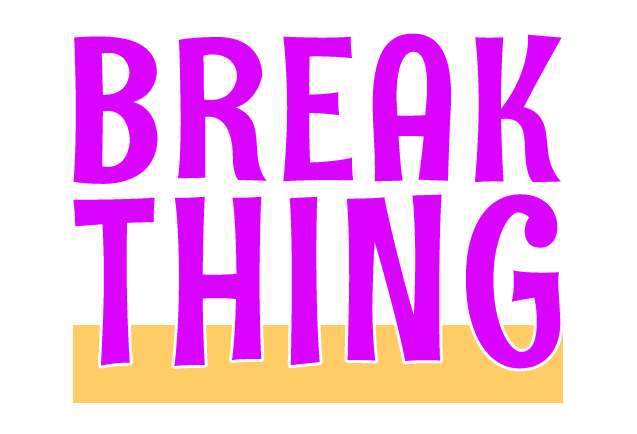用人類學視角來看待金融危機|巴倫讀書會
1年前

用人類學視角來看待金融危機|巴倫讀書會
如果有更多銀行家像人類學家那樣思考,他們就不會對日益增長的風險視而不見。
編者按人們通常以爲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亞馬遜叢林裏的原始部落,但是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金融時報》專欄記者吉蓮邰蒂卻將人類學的眼光投向了現代社會的專業群體,包括被她稱爲“彭博村”居民的金融家們。 她發現,金融界像原始部落一樣充滿了儀式和符號,但卻缺少了活生生的人,人類學視角可以爲他們提供一面鏡子,這也許就是格林斯潘也希望理解人類學的原因。本文選摘自吉蓮邰蒂的《視角:鳥瞰與蟲眼》第4章《金融危機》。
 法國裏維埃拉海岸的尼斯市,我坐在一個現代主義市政廳的黑暗會議室的後排,感覺自己很傻。我旁邊坐着一排身穿中式襯衫和粉色襯衫的人。他們的脖子上掛着大塑料繩系着的名牌,上面寫着“2005 年歐洲證券化論壇”。這是一個交易復雜金融工具的銀行家的聚會,這些金融工具包括與抵押貸款和公司貸款有關的衍生工具。我作爲《金融時報》的記者,在那裏進行報道。 在大廳前部的講台上,金融家們正在討論他們業內的創新成果,刷新着印有方程式、圖表、希臘字母以及“CDO”“CDS”“ABS”和“CLO”等縮寫的演示文稿。我感到一種文化衝擊,這比在塔吉克斯坦時要微妙得多,因爲文化模式感覺更熟悉,但語言對我來說是天方夜譚。 我不知道 “CDO”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論壇上在發生什么。我當時想,一個投資銀行會議就像一個塔吉克婚禮。一群人正在使用儀式和符號來創造和加強他們的社會關系和世界觀。在塔吉克斯坦是以一個復雜的婚禮儀式、舞蹈和刺繡墊子的禮物的形式呈現。在法國裏維埃拉,則是銀行家們交換名片、喝酒、开玩笑,進行共同的高爾夫之旅,並在黑暗的會議室裏觀看幻燈片。但這兩種情況下的這些儀式和符號都反了一個共同的認知地圖、偏見和假設。 “彭博村”的金融家們 因此,當我坐在黑暗的法國會議廳裏時,我試圖“閱讀”支撐會議的象徵性地圖,就像我曾經試圖“閱讀”塔吉克婚禮上的象徵意義,即格爾茨的架構下的“意義之網”,注意人們沒有談論的內容,以及他們想要討論的話題。規律漸漸浮現出來了。金融家們認爲他們控制着一種語言和知識,而其他人很少有機會接觸這種語言和知識,這使他們感到自己是精英。 當我要求一位金融家解釋什么是“CDO”或“CDS”時,他开玩笑說:“在我的銀行裏,幾乎也沒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學到了,它們分別代表“抵押債務”和“信用違約互換”。)金融家們擁有這種共同的語言,這就形成了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被知識的紐帶和通過工作形成的圈子聯系在一起,盡管他們在紐約、倫敦、巴黎、蘇黎世和中國香港等不同的地方工作。他們通過一個連接到彭博交易終端的專用信息系統進行交流。 我對自己开玩笑說,這就像一個“彭博村”。爲了證明他們活動的意義,金融家們還有一個獨特的“創造神話”(另一個常見的人類學術語)。局外人有時聲稱,金融家只是爲了賺錢而從事他們的工作。 然而,銀行家們並沒有以這種自我方式展示他們的活動。相反,他們引進了“效率”“流動性”和“創新”等概念。證券化設計背後的創造故事——這也是會議的主題——這個過程使市場更具“流通”,即債務和風險可以像水一樣容易交易和流通,使借錢更便宜。他們堅持認爲這對金融家和非金融家都有好處。 另一個凸顯事實的細節是,金融家們的演示文稿缺乏一個特點:臉或其他真人的圖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似乎很奇怪,因爲創世神話宣稱“創新”使普通人受益。但當金融家們談論他們的技藝時,他們很少提到活生生的人。希臘字母、縮略語、算法和圖表充斥着他們的演示文稿。這些錢是誰借來的?人在哪裏?這與現實生活有什么聯系? 起初,這些問題讓我感到好奇,而不是警覺。人類學思維方式的一個特徵——像新聞學一樣——是強迫性好奇,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剛跌入了一個全新的呼喚着我去探索的領域。我告訴自己,如果自己开始爲這片陌生的領域寫下旅行指南,對《金融時報》的讀者來說可能是有價值的,假想自己可能會像同事報道硅谷那樣報道金融。畢竟,這兩個行業都有一個創造神話,即宣揚關於創新及其帶給人類所謂的好處。 後來人們發現,借用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後來的說法,這個創造神話也包含了一個可怕的“缺陷”;我在裏維埃拉觀察到的文化正在創造風險,後來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風險。正因爲金融家是一個緊密相連,幾乎沒有外部監督的知識分子部落,所以他們無法看到他們的創造是否失去控制。而且,由於他們對創新的好處有如此強烈的“創造神話”執念,他們對風險視而不見。 一位名叫丹尼爾貝恩扎的人類學家後來把這個問題稱爲“基於模型的道德脫離”;另一位名叫凱倫何的人把它歸咎於“流動性崇拜”;還有一位名叫文森特萊比奈的人強調了對復雜數學的“掌握”。 不管用什么比喻,問題是金融家們既看不到他們所做事情的外部環境(廉價貸款對借款人的影響),也看不到他們世界的內部環境(他們的小圈子性質和特殊激勵計劃如何助長風險)。 這就是爲什么人類學視野很重要。人類學的一個好處是,它可以讓人們對陌生的“他者”產生共鳴。另一個好處是,它可以爲熟悉的我們提供一面照照自己的鏡子。在“熟悉”和“陌生”之間劃清界限從來都不容易。文化差異存在於一個不斷變化的譜系上,而不是僵硬的靜態框架。 但關鍵的一點是:無論你在哪裏,無論你處於何種熟悉和陌生的混合體中,停下來問自己一個裏維埃拉的銀行家們並沒有問的簡單問題總是有好處的:如果我作爲一個完全的陌生人,或者作爲一個火星人或孩童,來到這一文化中,我可能會看到什么? 爲什么格林斯潘希望了解人類學 2011年,我遇到了格林斯潘,這位傳奇人物曾在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聯儲。我們當時在阿斯彭思想大會上,這個會議每年都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同名小鎮舉行。他問我在哪裏可以找到一本關於人類學的好書。“人類學?”我驚訝地反問。 在這之前,這位強大的前中央銀行家——因爲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而被稱爲“大師”——似乎是最不可能對文化研究感興趣的人。他是相信自由市場理論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群體的縮影,他們認爲人類是由追求利潤和理性的自我利益驅動的,理性到可以用牛頓物理學的模型來追蹤。 這種立場促使格林斯潘支持金融創新,並對此採取不聞不問的政策;即使他擔心信貸衍生工具或其他領域會出現泡沫,他也認爲這些泡沫會自我糾正,因爲市場是流通和有效的。 盡管他偶爾會對衍生工具的內在風險提出警告,但他同意金融家的觀點,即抵押債務和信用違約互換等產品會使市場更有“流動性”和效率,因此,他對這些產品表示贊同。 我問他爲什么想了解人類學,格林斯潘帶着狡黠的微笑指出,世界已經改變,他想了解它。這似乎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2007 年夏天,在債務鏈中的一些債權人——如美國抵押貸款借款人—— 开始出現違約後,金融危機爆發了。這些違約的最初損失並不是很大。然而,它們在金融方面造成了相當於食物中毒的恐慌,很容易再一次用香腸的比喻來解釋:如果一小塊爛肉進入了屠夫的攪拌機,消費者就會避开所有的碎肉和香腸,因爲他們無法判斷毒物可能在哪裏。 當抵押貸款出現違約時,投資人拒絕觸碰任何抵押債務,因爲他們無法跟蹤風險,因爲這些工具已經被切割了很多次。本應在投資者之間分散風險,從而使其更容易緩衝打擊的金融工具,爲系統引入了新的風險——信心的喪失。沒有人知道風險去了哪裏。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金融當局爭先恐後地解決這個“金融食物中毒”的問題,解決辦法是支撐市場,救助銀行,然後隔離(和清除)包含不良抵押貸款或“毒藥”的金融工具。然而這並不奏效:2008年 10 月,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爆發了。 這對格林斯潘等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認知打擊。整整一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自由市場的經濟激勵機制可以創造出如此高效的金融體系,以至於如果出現任何過度行爲,比如信貸泡沫,它們都會自我糾正,不會造成真正的損害。現在看來這是錯的。或者正如格林斯潘在 2008 年底告訴國會的那樣。“我的思維上有缺陷。”這就是爲什么他想讀一些關於人類學的書:他想知道“文化”是如何擾亂這些模型的。 我被打動了。當格林斯潘第一次向國會發表承認“缺陷”的評論時,這一承認引發了廣泛的嘲諷,特別是那些在崩盤中損失了資金的人。但我認爲這種反應是不合適的,任何領導人,更不用說被稱爲“大師”的人,都很少在公开場合承認知識上的錯誤。更少有人會試圖通過探索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如人類學,來重新思考他們的想法。 我認爲格林斯潘在擁抱一種探索精神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我們討論人類學時,我也意識到,格林斯潘想了解“文化”的原因與大多數人類學家的動力不盡相同。對他來說,研究“文化”主要是試圖理解爲什么其他人會有奇怪的行爲。因此,他轉向人類學的原因與惠蒂在英國面對埃博拉病毒期間向人類學家尋求幫助的原因相同:了解“奇怪”的其他人。 當我在阿斯彭遇到他時,格林斯潘特別好奇的是文化模式如何影響比如 2011 年的歐債危機,他覺得希臘人的行爲特別令人困惑。換言之,希臘人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奇怪的“他者”,特別是將他們與德國人相比時,他想知道希臘人的文化模式是否會使歐元區崩潰。 學會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 這是一個合理的擔憂。人類學家經常探索“他者”。但這只是人類學所能提供的一半知識,在 2008 年之後,不僅是希臘提供了有趣的文化分析材料;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剛剛發生的債務問題也同樣有趣。所以我建議他讀一些人類學家對西方金融所做的研究。有很多可供選擇的研究方案。例如,人類學家凱特琳扎魯姆(Caitlin Zaloom)曾在2000年與芝加哥交易市場和倫敦市場的交易市場人員一起生活,並跟蹤了傳統交易向電子交易的轉變是如何影響金融家的文化。 何凱倫解構了華爾街的流動性意識形態,並指出,金融業不斷失控的一個關鍵原因是金融家們將這種框架移植到了實體經濟中——卻沒有意識到這在其他人看來是多么的奇怪,甚至不合適。 據她的觀察:“我的華爾街信源沒有認識到,不斷的交易和瘋狂的員工流動性是華爾街的獨有文化,而是將他們的操作實踐與他們作爲市場解讀者的文化角色混在一起。他們混淆了‘自然的’市場規律和金融周期。” 同樣,蘇格蘭金融社會學家唐納德麥肯齊分析了交易員的部落主義如何促使他們爲金融產品建立不同的估值模型,即使是用同樣的所謂“中立”的數據進行計算。一位美國法律人類學家——將人類學應用於法律的人——安利斯瑞爾斯(Annelise Riles)對日本和美國的衍生工具合同對文化的意義做了驚人的分析。 另一位名叫梅麗莎費舍爾(Melissa Fisher)的法律人類學家分析了圍繞華爾街性別不平衡的特殊問題。丹尼爾蘇萊爾斯(Daniel Souleles)研究了私募股權玩家的網絡。亞歷山大勞莫尼耶(Alexandre Laumonier)做了一項引人入勝的工作,研究手機信號塔的位置如何影響芝加哥和倫敦的對衝基金的交易策略。 另一位法語人類學家萊比奈在一家法國銀行擔任股票衍生品交易員,他寫了一份出色的研究報告,闡明了即使是金融家也很難理解的“破壞性的金融工程”和“創新金融產品產生的風險”。 正如人類學家凱斯哈特(Keith Hart)所言,有大量的研究試圖以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來考慮宏觀經濟模型,並將經濟嵌入社會生活之中。甚至還有一項針對格林斯潘“部落”的出色研究。 美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霍姆斯(Douglas Holmes)曾研究英格蘭銀行、瑞典銀行和新西蘭儲備銀行等機構的禮儀,並得出結論:中央銀行家們對經濟施加(或施加了)影響,不是通過機械地改變貨幣價格(正如經濟學家的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樣),而是通過施展“口頭咒語”。因此敘事和文化很重要,即使對中央銀行家來說也是如此;其實,敘事和文化對央行來說尤其重要。 然而,正因爲精英們很難“翻轉鏡頭”,所以尤爲重要。這一點在新冠病毒的故事中得到驗證。在金錢的世界裏也是如此。如果金融家們在 2008 年之前以人類學家的視角來操作,金融泡沫可能永遠不會變得如此之大,然後以如此可怕的後果破裂。 同樣,如果有更多的中央銀行家、監管者、政治家以及記者能夠像人類學家那樣思考,他們就不會對日益增長的風險視而不見,也不會對銀行家如此信任。 《視角:鳥瞰與蟲眼》 原名:Anthro-Vision 作者:吉蓮邰蒂 譯者:董子維 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 66
法國裏維埃拉海岸的尼斯市,我坐在一個現代主義市政廳的黑暗會議室的後排,感覺自己很傻。我旁邊坐着一排身穿中式襯衫和粉色襯衫的人。他們的脖子上掛着大塑料繩系着的名牌,上面寫着“2005 年歐洲證券化論壇”。這是一個交易復雜金融工具的銀行家的聚會,這些金融工具包括與抵押貸款和公司貸款有關的衍生工具。我作爲《金融時報》的記者,在那裏進行報道。 在大廳前部的講台上,金融家們正在討論他們業內的創新成果,刷新着印有方程式、圖表、希臘字母以及“CDO”“CDS”“ABS”和“CLO”等縮寫的演示文稿。我感到一種文化衝擊,這比在塔吉克斯坦時要微妙得多,因爲文化模式感覺更熟悉,但語言對我來說是天方夜譚。 我不知道 “CDO”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論壇上在發生什么。我當時想,一個投資銀行會議就像一個塔吉克婚禮。一群人正在使用儀式和符號來創造和加強他們的社會關系和世界觀。在塔吉克斯坦是以一個復雜的婚禮儀式、舞蹈和刺繡墊子的禮物的形式呈現。在法國裏維埃拉,則是銀行家們交換名片、喝酒、开玩笑,進行共同的高爾夫之旅,並在黑暗的會議室裏觀看幻燈片。但這兩種情況下的這些儀式和符號都反了一個共同的認知地圖、偏見和假設。 “彭博村”的金融家們 因此,當我坐在黑暗的法國會議廳裏時,我試圖“閱讀”支撐會議的象徵性地圖,就像我曾經試圖“閱讀”塔吉克婚禮上的象徵意義,即格爾茨的架構下的“意義之網”,注意人們沒有談論的內容,以及他們想要討論的話題。規律漸漸浮現出來了。金融家們認爲他們控制着一種語言和知識,而其他人很少有機會接觸這種語言和知識,這使他們感到自己是精英。 當我要求一位金融家解釋什么是“CDO”或“CDS”時,他开玩笑說:“在我的銀行裏,幾乎也沒有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學到了,它們分別代表“抵押債務”和“信用違約互換”。)金融家們擁有這種共同的語言,這就形成了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被知識的紐帶和通過工作形成的圈子聯系在一起,盡管他們在紐約、倫敦、巴黎、蘇黎世和中國香港等不同的地方工作。他們通過一個連接到彭博交易終端的專用信息系統進行交流。 我對自己开玩笑說,這就像一個“彭博村”。爲了證明他們活動的意義,金融家們還有一個獨特的“創造神話”(另一個常見的人類學術語)。局外人有時聲稱,金融家只是爲了賺錢而從事他們的工作。 然而,銀行家們並沒有以這種自我方式展示他們的活動。相反,他們引進了“效率”“流動性”和“創新”等概念。證券化設計背後的創造故事——這也是會議的主題——這個過程使市場更具“流通”,即債務和風險可以像水一樣容易交易和流通,使借錢更便宜。他們堅持認爲這對金融家和非金融家都有好處。 另一個凸顯事實的細節是,金融家們的演示文稿缺乏一個特點:臉或其他真人的圖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似乎很奇怪,因爲創世神話宣稱“創新”使普通人受益。但當金融家們談論他們的技藝時,他們很少提到活生生的人。希臘字母、縮略語、算法和圖表充斥着他們的演示文稿。這些錢是誰借來的?人在哪裏?這與現實生活有什么聯系? 起初,這些問題讓我感到好奇,而不是警覺。人類學思維方式的一個特徵——像新聞學一樣——是強迫性好奇,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剛跌入了一個全新的呼喚着我去探索的領域。我告訴自己,如果自己开始爲這片陌生的領域寫下旅行指南,對《金融時報》的讀者來說可能是有價值的,假想自己可能會像同事報道硅谷那樣報道金融。畢竟,這兩個行業都有一個創造神話,即宣揚關於創新及其帶給人類所謂的好處。 後來人們發現,借用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後來的說法,這個創造神話也包含了一個可怕的“缺陷”;我在裏維埃拉觀察到的文化正在創造風險,後來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風險。正因爲金融家是一個緊密相連,幾乎沒有外部監督的知識分子部落,所以他們無法看到他們的創造是否失去控制。而且,由於他們對創新的好處有如此強烈的“創造神話”執念,他們對風險視而不見。 一位名叫丹尼爾貝恩扎的人類學家後來把這個問題稱爲“基於模型的道德脫離”;另一位名叫凱倫何的人把它歸咎於“流動性崇拜”;還有一位名叫文森特萊比奈的人強調了對復雜數學的“掌握”。 不管用什么比喻,問題是金融家們既看不到他們所做事情的外部環境(廉價貸款對借款人的影響),也看不到他們世界的內部環境(他們的小圈子性質和特殊激勵計劃如何助長風險)。 這就是爲什么人類學視野很重要。人類學的一個好處是,它可以讓人們對陌生的“他者”產生共鳴。另一個好處是,它可以爲熟悉的我們提供一面照照自己的鏡子。在“熟悉”和“陌生”之間劃清界限從來都不容易。文化差異存在於一個不斷變化的譜系上,而不是僵硬的靜態框架。 但關鍵的一點是:無論你在哪裏,無論你處於何種熟悉和陌生的混合體中,停下來問自己一個裏維埃拉的銀行家們並沒有問的簡單問題總是有好處的:如果我作爲一個完全的陌生人,或者作爲一個火星人或孩童,來到這一文化中,我可能會看到什么? 爲什么格林斯潘希望了解人類學 2011年,我遇到了格林斯潘,這位傳奇人物曾在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聯儲。我們當時在阿斯彭思想大會上,這個會議每年都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同名小鎮舉行。他問我在哪裏可以找到一本關於人類學的好書。“人類學?”我驚訝地反問。 在這之前,這位強大的前中央銀行家——因爲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而被稱爲“大師”——似乎是最不可能對文化研究感興趣的人。他是相信自由市場理論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群體的縮影,他們認爲人類是由追求利潤和理性的自我利益驅動的,理性到可以用牛頓物理學的模型來追蹤。 這種立場促使格林斯潘支持金融創新,並對此採取不聞不問的政策;即使他擔心信貸衍生工具或其他領域會出現泡沫,他也認爲這些泡沫會自我糾正,因爲市場是流通和有效的。 盡管他偶爾會對衍生工具的內在風險提出警告,但他同意金融家的觀點,即抵押債務和信用違約互換等產品會使市場更有“流動性”和效率,因此,他對這些產品表示贊同。 我問他爲什么想了解人類學,格林斯潘帶着狡黠的微笑指出,世界已經改變,他想了解它。這似乎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2007 年夏天,在債務鏈中的一些債權人——如美國抵押貸款借款人—— 开始出現違約後,金融危機爆發了。這些違約的最初損失並不是很大。然而,它們在金融方面造成了相當於食物中毒的恐慌,很容易再一次用香腸的比喻來解釋:如果一小塊爛肉進入了屠夫的攪拌機,消費者就會避开所有的碎肉和香腸,因爲他們無法判斷毒物可能在哪裏。 當抵押貸款出現違約時,投資人拒絕觸碰任何抵押債務,因爲他們無法跟蹤風險,因爲這些工具已經被切割了很多次。本應在投資者之間分散風險,從而使其更容易緩衝打擊的金融工具,爲系統引入了新的風險——信心的喪失。沒有人知道風險去了哪裏。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裏,金融當局爭先恐後地解決這個“金融食物中毒”的問題,解決辦法是支撐市場,救助銀行,然後隔離(和清除)包含不良抵押貸款或“毒藥”的金融工具。然而這並不奏效:2008年 10 月,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爆發了。 這對格林斯潘等人來說是一個痛苦的認知打擊。整整一代的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自由市場的經濟激勵機制可以創造出如此高效的金融體系,以至於如果出現任何過度行爲,比如信貸泡沫,它們都會自我糾正,不會造成真正的損害。現在看來這是錯的。或者正如格林斯潘在 2008 年底告訴國會的那樣。“我的思維上有缺陷。”這就是爲什么他想讀一些關於人類學的書:他想知道“文化”是如何擾亂這些模型的。 我被打動了。當格林斯潘第一次向國會發表承認“缺陷”的評論時,這一承認引發了廣泛的嘲諷,特別是那些在崩盤中損失了資金的人。但我認爲這種反應是不合適的,任何領導人,更不用說被稱爲“大師”的人,都很少在公开場合承認知識上的錯誤。更少有人會試圖通過探索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如人類學,來重新思考他們的想法。 我認爲格林斯潘在擁抱一種探索精神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我們討論人類學時,我也意識到,格林斯潘想了解“文化”的原因與大多數人類學家的動力不盡相同。對他來說,研究“文化”主要是試圖理解爲什么其他人會有奇怪的行爲。因此,他轉向人類學的原因與惠蒂在英國面對埃博拉病毒期間向人類學家尋求幫助的原因相同:了解“奇怪”的其他人。 當我在阿斯彭遇到他時,格林斯潘特別好奇的是文化模式如何影響比如 2011 年的歐債危機,他覺得希臘人的行爲特別令人困惑。換言之,希臘人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奇怪的“他者”,特別是將他們與德國人相比時,他想知道希臘人的文化模式是否會使歐元區崩潰。 學會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 這是一個合理的擔憂。人類學家經常探索“他者”。但這只是人類學所能提供的一半知識,在 2008 年之後,不僅是希臘提供了有趣的文化分析材料;華爾街或倫敦金融城剛剛發生的債務問題也同樣有趣。所以我建議他讀一些人類學家對西方金融所做的研究。有很多可供選擇的研究方案。例如,人類學家凱特琳扎魯姆(Caitlin Zaloom)曾在2000年與芝加哥交易市場和倫敦市場的交易市場人員一起生活,並跟蹤了傳統交易向電子交易的轉變是如何影響金融家的文化。 何凱倫解構了華爾街的流動性意識形態,並指出,金融業不斷失控的一個關鍵原因是金融家們將這種框架移植到了實體經濟中——卻沒有意識到這在其他人看來是多么的奇怪,甚至不合適。 據她的觀察:“我的華爾街信源沒有認識到,不斷的交易和瘋狂的員工流動性是華爾街的獨有文化,而是將他們的操作實踐與他們作爲市場解讀者的文化角色混在一起。他們混淆了‘自然的’市場規律和金融周期。” 同樣,蘇格蘭金融社會學家唐納德麥肯齊分析了交易員的部落主義如何促使他們爲金融產品建立不同的估值模型,即使是用同樣的所謂“中立”的數據進行計算。一位美國法律人類學家——將人類學應用於法律的人——安利斯瑞爾斯(Annelise Riles)對日本和美國的衍生工具合同對文化的意義做了驚人的分析。 另一位名叫梅麗莎費舍爾(Melissa Fisher)的法律人類學家分析了圍繞華爾街性別不平衡的特殊問題。丹尼爾蘇萊爾斯(Daniel Souleles)研究了私募股權玩家的網絡。亞歷山大勞莫尼耶(Alexandre Laumonier)做了一項引人入勝的工作,研究手機信號塔的位置如何影響芝加哥和倫敦的對衝基金的交易策略。 另一位法語人類學家萊比奈在一家法國銀行擔任股票衍生品交易員,他寫了一份出色的研究報告,闡明了即使是金融家也很難理解的“破壞性的金融工程”和“創新金融產品產生的風險”。 正如人類學家凱斯哈特(Keith Hart)所言,有大量的研究試圖以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來考慮宏觀經濟模型,並將經濟嵌入社會生活之中。甚至還有一項針對格林斯潘“部落”的出色研究。 美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霍姆斯(Douglas Holmes)曾研究英格蘭銀行、瑞典銀行和新西蘭儲備銀行等機構的禮儀,並得出結論:中央銀行家們對經濟施加(或施加了)影響,不是通過機械地改變貨幣價格(正如經濟學家的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樣),而是通過施展“口頭咒語”。因此敘事和文化很重要,即使對中央銀行家來說也是如此;其實,敘事和文化對央行來說尤其重要。 然而,正因爲精英們很難“翻轉鏡頭”,所以尤爲重要。這一點在新冠病毒的故事中得到驗證。在金錢的世界裏也是如此。如果金融家們在 2008 年之前以人類學家的視角來操作,金融泡沫可能永遠不會變得如此之大,然後以如此可怕的後果破裂。 同樣,如果有更多的中央銀行家、監管者、政治家以及記者能夠像人類學家那樣思考,他們就不會對日益增長的風險視而不見,也不會對銀行家如此信任。 《視角:鳥瞰與蟲眼》 原名:Anthro-Vision 作者:吉蓮邰蒂 譯者:董子維 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 66 文|吉蓮邰蒂
編輯|彭韌
版權聲明: 《巴倫周刊》(barronschina)原創文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本文內容僅供參考,投資建議不代表《巴倫周刊》傾向;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
追加內容
本文作者可以追加內容哦 !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標題:用人類學視角來看待金融危機|巴倫讀書會
地址:https://www.breakthing.com/post/47046.html